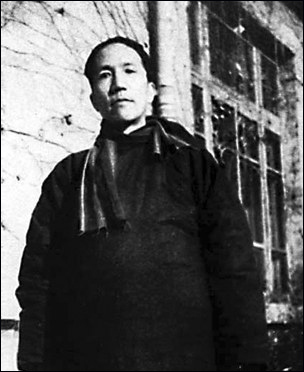
陳寅恪
2013、2014這兩年🐁,坊間出版發行研究陳寅恪的著作多達十五種(估計還有筆者不曾知曉的遺珍)🏌🏻。其中三種是舊版書增補修訂重印𓀊,即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下稱《二十年》)✌🏿,吳定宇的《學人魂·陳寅恪傳》(下稱《學人魂》)🌞,吳學昭的《吳宓與陳寅恪》。這三本書對引發上世紀90年代中期“陳寅恪熱”功不可沒。二十年過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三書都增補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見解🏌🏼♀️,尤以《學人魂》為最🚶🚵🏿♀️。
《學人魂》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初版於1996年8月🖕🏿🎬,印數五千冊,次年4月重印,增加到九千冊。這個印數在出版業開始企業經營、純學術著作出書越來越難的形勢下差強人意,但比起此前八個月三聯書店出版的《二十年》兩年重印六次,印數八萬冊來👸🏼,自然有大小巫之喻。2013年6月《二十年》修訂本首印五萬冊👩🏽🚀,很快售罄,不得不加印。2014年11月《學人魂》改書名為《守望·陳寅恪往事》(下稱《守望》),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字數從18萬字擴充到53萬字,可謂面目一新,但影響力似乎不如原書《學人魂》大。筆者查閱“超星讀秀學術搜索”提供的各地圖書館收藏情況🤘🏿,1996年的《二十年》收藏單位為351家,修訂本140家;1996年的《學人魂》170家,《守望》只有12家。這個收藏資料與《守望》的學術質量極不相稱。
原書名《學人魂·陳寅恪傳》傳神地概括歸納了傳主陳寅恪的學術地位✊🏻🧝🏿♀️、人格風貌和時代精神。“學人魂”是文化學術界繼魯迅的“民族魂”稱號之後,對中國近世又一個傑出知識分子代表的贊頌,陳寅恪作為一代史學大師和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道德良心的楷模,“學人魂”當之無愧。而新書名《守望·陳寅恪往事》的中心主旨本意是弘揚陳寅恪守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園,但從封面上“守望·陳寅恪往事”字樣看不出此書深刻的含義。作者在原書《學人魂》的基礎上增加了那麽多新材料,對陳寅恪的認識理解也頗樹新義,卻舍棄了“學人魂”這麽好的創意🛸🧑🏿🍳,淡化了與“陳寅恪熱”的後續聯系,誠為作者惜👨🏿🔬,亦為此書惜。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陳寅恪熱”興起後,關於陳寅恪的家世、生平👨👩👧、學術的讀物層出不窮🧛♀️。其中由余英時開先河的陳寅恪晚年心路歷程的研究令人矚目,《二十年》的作者抓住這個節點🕺🏽,把這項研究推向了高潮。這本以陳寅恪晚年經歷為切入點的傳記🦫,作者發掘了數量可觀的內部檔案史料🙋🏼♂️,有石破天驚的社會反映。
《學人魂》雖然沒有像《二十年》那樣從陳寅恪的晚年切入展開,而是平鋪直敘傳主的一生,但此書關於陳寅恪晚年的部分仍可圈可點⚄。由於作者任教於中山大學(下稱“中大”),並任學報社科版主編🤶,能夠看到中大檔案館的檔案和獲得一些中大老人的口述資料。兩書作者同在廣州,差不多同時起步寫陳寅恪🐫,《學人魂》出版時間慢了半拍🙇🏿♂️。如果說1996年因《二十年》發射出的毫光,其它的陳寅恪傳記都有“燈下黑”現象的話👩🏼,那麽《學人魂》的作者後來獲得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契機🦸🏽。2003年,中大慶祝建校八十周年,請他領銜撰寫一部新校史🙎🏻♂️🧑🏻🚀,可以查閱使用校檔案館的解密檔案和圖書館的任何書籍。相對於以前有條件的查閱檔案,作者擁有了大量第一手珍貴資料🚒🤷🏽♀️。
查閱《學人魂》第五章《嶺南晚景》尾註,可知作者當年使用中大檔案只有十余處🔲,而《守望》增加到四十余處,加上口述資料和作者廣泛搜集近些年出版的與陳寅恪有關人物的日記🤵🏻♂️、書信、文集⏏️、回憶錄以及其它材料🈁,使《守望》的第四章《康樂風雨》、第五章《桑榆暮景》材料豐富,內容充實🧖🏿♂️,篇幅上也占了全書一半🙇♀️。舉凡陳寅恪晚年的熱點話題如堅不去國、拒返北都、思想言論✯、國寶待遇、政要來訪👱♀️、師門恩怨、遭受批判🎈、“文革”劫難等,都有新材料、新論述呈現展示。
關於陳寅恪拒迎北返任職的史實🦴,作者使用了中大檔案和親歷親聞此事者的書信🎲、日記和口述資料🧏🏽♂️,鉤沉探微,把前因後果、各方反映梳理得清晰切實。1953年11月🦖,陳門弟子汪篯南下廣州勸說老師北返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中古所所長。汪篯非社科院人員,由他來勸顯然持有“尚方寶劍”,因此🧍🧏🏽♀️,陳寅恪口述的《對科學院的答復》就不是一般的態度陳述。在這份文獻中,陳寅恪重申自己1929年所寫《王國維紀念碑銘》中抵製國民黨思想桎梏的思想理念:“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不能研究學術”🗽,並開出北返就職的條件👩🏼🍼。這份文獻的挖掘面世,為二十世紀學術史和思想史作出了貢獻🧖🏽♀️🍵。《守望》作者再次細讀這份文獻,增補了記錄者的一段原話:“這是陳寅恪的談話,全部發言不能完全照錄💆🏼,因為記不下來。但大致不差,原意決無出入。”並對筆跡進行了比對,認定這是在中大任教的另一位陳門弟子金應熙抄錄的副本,理清了這份文獻的版本源流。日後汪篯的正本若浮出水面🧔♀️💋,圍繞此事可能還有新的言說🩰。
陳寅恪這次拒返後🟧,中央仍未放棄敦促他進京的計劃。據2006年出版的《吳宓日記續編》,1956年3月6日,劉文典從北京返回昆明,先到成都,與吳宓見面。劉談了他這次進京的使命🚣🏼♂️,政府請他作說客勸陳寅恪北返🖥,劉轉請吳代他去廣州完成這一任務🛁。3月10日,吳復函劉🥉👆🏻,告知他不擬赴廣州做說客。
陳寅恪在1949年南下之前👩🎤,已經譽滿士林。其世家子弟的身世,教育部部聘教授、牛津大學聘任教授、中研院院士的身份,留學列國、通曉多門外語、教授的教授、目盲著書、記憶力驚人等等傳聞,使他身上籠罩著一層神秘的光環。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大教務長在一份“關於陳寅恪”的報告中反映“四年級學生如陳仿、鄒文光、曹國祉等對陳寅恪甚為崇拜,曹曾表示🙍,替陳掃地服役,亦甚願意……校外的一些中學生⏸,聽說中大有一個國寶級的教授🙅♂️,認識十幾種文字,到處打聽他住在什麽地方💱,究竟懂得哪些國家的文字。羨慕他不用馬列主義也能贏得人們的尊重👨🏼⚕️,希望有朝一日能列其門下”。
陳寅恪“國寶”待遇首先是他的社會地位得到中央的關照🏊🏼♀️。1954年夏秋之際,中國社科院籌備成立“學部”時🫰🏽✌🏿,對是否遴選陳寅恪任學部委員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據主持其事的副院長張嫁夫回憶:“矛盾最尖銳的是陳寅恪,他是史學界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不行,他下邊的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一再申稱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五五年第二屆全國政協均邀請陳寅恪擔任代表、委員🧚♀️,中大黨委書記馮乃超多次上門做工作🏊🏻♀️,均遭婉拒。後同意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一個名義,但不赴京開會👷🏼。
另一個關於陳寅恪待遇的熱門話題是對他生活上的特殊照顧。1956年,陳寅恪評為一級教授(中大初評意見為“特級”)🛌🏿。這一年中大還給予陳寅恪配助手、付特級稿費🚨、可以使用中大僅有的兩輛小汽車等照顧👨🏽🎤。1962年7月陳寅恪右腿骨折住院和出院後的特護🔎,享受了省級領導也不一定有的待遇(醫療方案由周恩來裁定,廣東省委批轉有關部門按月供應營養食品,配三個半護士🧑🏻⚕️,陶鑄特別關照購買落地式收音機等)。
對陳寅恪晚年獲得的優待禮遇🧑🏽🎄,社會上口耳相傳👨🏿🦱,但陳寅恪本人精神上卻常感痛苦壓抑🧛🏿。1964年在《廣州贈蔣天樞序》中宣稱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1969年中大的一份“形勢報告”揭發陳寅恪“聲稱不為五鬥米折腰,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正可移來作他“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的註腳🥻。
中大一直有聲音對陳寅恪享受特殊照顧忿忿不平。《守望》作者解釋背後的原因🤶🏽,是中央把他列為重要的統戰對象,《中國統一戰線全書》立有《陳寅恪小傳》◻️,可以印證這個說法🤦🏿。中共建政後,高層對文化、教育、藝術🦻、科技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實行政治上予以保護、生活上厚待、思想上不要求立刻轉變立場觀點的特殊政策。此外,港臺報刊經常拿陳寅恪的現狀說事,促使當局更加尊禮陳寅恪,以反證港臺報紙失實。
然而從中大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保存下來的那麽多關於陳寅恪的內部材料來看⏲,陳在享受極高禮遇的同時🦍😛,他的政治態度和言論(包括詩作🪞👩🏽🦱、對聯),常常被人通過不同途徑反映到校黨委和廣東省委有關部門。對他著作出版的審查也很嚴格💇🏿。這些動作,陳寅恪不可能洞悉其內情💚,但他從校園內部和周邊社會能感覺得出時局動態和運動的氛圍,在心境上不可能置身事外。直到1961年8月,老友吳宓間關遠道來探望他🌯,才獲得一次披心見素的宣泄管道😶。
陳寅恪這種既受禮遇又被另類的復雜詭譎、充滿秘辛的現象🔍,給中大校方和歷史系主政者帶來考驗。1949年幹戈擾攘之際🧝🏿♂️,陳寅恪南下定居,對中大的意義非同小可。由於陳寅恪在學界的崇高地位🧒🏼,中國的大學和學術機構都以延攬他為首選目標🐇。他既不浮海也不北返,對中大是極大的支持。站在學校地位、聲望的角度,中大需要這塊“金字招牌”,給予保護🔷、照顧,但陳寅恪獨立,始終不與意識形態合拍。在陳寅恪的晚年,一次又一次的運動無不以改造思想為主要目標📺,而陳寅恪以目盲🌙、多病為由從不參加🧑🏿🏭。在這種局面下📇,保他的人首先面臨著站穩立場的壓力,整他的人疏於分析紛繁錯綜的格局和掂量陳寅恪的份量,碰到了“硬釘子”。
1957年的“反右”運動,陳寅恪未受沖擊,以他的言論和思想傾向,在當時的氣候中,已屬特例。《守望》增補了不少陳寅恪1957年前的言論,如他寫“八股文章試帖詩,宗朱頌聖有成規。白頭宮女哈哈笑,眉樣如今又入時”詩後👋🏼🦸🏽,曾對人解釋說:“人人都宗朱頌聖,我則不能。宗朱猶可,頌聖則決不可🏘🦮。”1958年,在“大躍進”中展開的“厚今薄古”“拔白旗”運動中🧑🏿🦱,陳寅恪成為全國文史學界聲討的人物。4月28日🎦,範文瀾發表《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一文。6月11日,郭沫若發表致北大歷史系師生的一封信,點了陳寅恪的名。於是各地批判“厚古薄今”運動如火如荼👩🏻🦯➡️,“拔白旗,插紅旗”的口號風行一時🤦🏽。當時中國社科院文研所製定了以王國維、陳寅恪為批判重點的規劃。浙江大學領導作報告,說今年須批判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等人。7月13日,中大召開批陳寅恪思想與學術大會👂🏽。會後,歷史系黨總支責成專人寫批判文章。8月🪬,中大製定“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五年規劃”👩🍳,把陳寅恪的繁瑣考證列為重點批判內容🦨🧻。歷史系組織師生在9月一個月內🎷,寫出批判文章71篇,其中批陳36篇🦮。廣東省委主辦的《理論與實踐》,本年第12期發表廣東批陳的壓卷之作《教授的教授》,矛頭不僅指向陳寅恪,而且指向崇拜他的人們。陳寅恪被批判後🥟,向校方提出不再上課,遷出中大。在陶鑄、杜國庠的過問下🏬,學校負責人多次勸慰🫃🏻,再三挽留🎇。陳同意不搬出校園,但堅持不再上課。《守望》作者用很長的篇幅對這次運動的背景、中大的布局、運動中發生的細節、陳門弟子的不同表現等往事鋪敘得淋漓盡致,使我們獲知不少歷史真相🈚️。
此後陳寅恪雖然不再開課授業🧑🏿🦱,但直到1969年10月他去世,始終被尊為中國史學界的泰鬥。1959年4月,被安排為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1960年7月經中央文史館館長章士釗提名,國務院批準,與沈尹默、商衍鎏👰🏿♂️、徐森玉榮膺副館長。這面“大白旗”不但沒有被拔倒,反而提高了知名度🤶🏿。《守望》第五章第二節《外地來客》增補了新材料。如作者使用存於北京郭沫若紀念館的《郭沫若日記》,得知郭於1961年3月13日和11月11日兩次到中大拜訪陳寅恪。盡管三年前郭點過陳的名,但陳不計前嫌接待了他。《日記》記錄了兩人見面時的氣氛和所談內容🖤,澄清了此前關於郭#️⃣、陳見面的一些可愛不可信的傳聞,啟發我們在言說考量陳、郭關系時🥟,註意處理好“無征不信”和“有聞必錄”這兩個寫歷史的原則。
1961年8月🤦♂️,比北京來訪更重要的一次會面來臨⭐️,陳寅恪至交吳宓來到陳宅。《守望》據《吳宓日記續編》增補了吳宓記錄的陳寅恪南下廣州後的思想信念🫅、風骨節操:“寅恪兄之思想與主張🧑⚕️🧗♂️,毫未改變,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確信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我輩本此信仰,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吳宓所記遠不止本文引錄的內容🪿,讀者可按讀《吳宓日記續編》原書)。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陳寅恪1929年寫《王國維紀念碑銘》🦙,1953年口述《對科學院的答復》,1961年與吳宓傾談,1964年寫《廣州贈蔣天樞序》貫穿起來,梳理出陳寅恪人文精神、學人風骨的主線脈絡。他一生始終如一守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守望中華文化之本位🏥。其學行人品道德文章,鑄就了近世“學人魂”☝🏼。論者有言👨🏼🍼,“一種思潮是否流行🧖🏻,取決於時代需要它的程度”(大意)。二十年前,人們呼喚“學人魂”,二十年後,人們還在呼喚“學人魂”✭🟧,研陳著作🤴🍶、文章出版發表勢頭仍然強勁,即是明證🪒。這是讀者看重“學人魂”這個創意🥛🧑🏻🏫,惟願《學人魂》增補本書名保留這個關鍵詞🤹🏻、重奏時代音符的終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