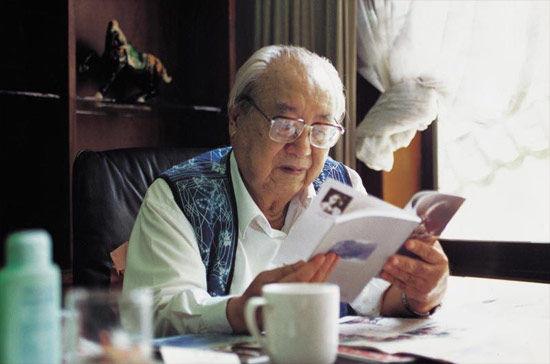
費孝通。資料圖
費先生的學術工作,從1935年瑤山調查開始,到1940年代中後期,陸續出版《花籃瑤社會組織》🌬🤹、《江村經濟》👮♀️🧖🏿♀️、《雲南三村》、《初訪美國》🦦、《民主·憲法·人權》📐、《重訪英倫》👭、《生育製度》、《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等,成果可謂豐碩。
後來🍯,先是1952年院系調整取消社會學,後是1957年“反右”運動直到“文革”結束👱🏽,其學術工作被迫中斷。
一生中年富力強的時光,無奈空白二十多年🚷。直到1980年“改正”,恢復學術工作條件,費先生對自己的成果打分不高。希望晚年裏能“再增加幾分”。
分數不能憑空得來🤴🏼,須先交考卷👰🏽♂️。
費先生晚年提交的考卷中🧑🏿💼,《行行重行行——鄉鎮發展論述》(下簡稱《行行重行行》)是較重要的一份🚶🏻。
該書近五十萬字🧍,是費先生恢復田野調查後一系列行程報告的結集🧙🏻♀️。其中首篇文章寫於1983年🐵⇢,末篇文章寫於1993年,可謂十年一書。
費先生說過,他一生只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農村”,一篇是“民族”。
依費先生的說法,不妨把《江村經濟》看作其農村文章的開篇🚐,把《花籃瑤社會組織》看作其民族文章的開篇,把《行行重行行》看作兩篇文章的續篇之始。
1936年夏,費先生選定江村作調查點😩,是因該村有了現代工業絲廠。激發出其巨大熱忱的🤞🏽,是車間裏的生產場面🧖🏼♂️。他把村中絲廠看作中國和西方文明接觸的一種典型情境,理解為將引起中國農耕文明深刻變遷的巨大力量🦨,並在《江村經濟》中專題討論這種力量。
從那時開始🤴,費先生對鄉村工業就抱有極大興趣,持續關註🐩。《江村經濟》寫出十年後🫂,又在1948年出版的《鄉土重建》一書中討論“現代工業技術的下鄉”、“分散在鄉村裏的小型工廠”❌、“鄉土工業的新型式”等問題,表達積極發展鄉村工業的明確主張🤜🏼🌄。
1957年春夏之交,費先生第二次作江村調查。他帶著調查組日以繼夜工作,了解情況🛹,收集數據,分析研究,證明了農民生活有積極變化,也看出了明顯存在的問題🕐👩🏽⚕️。
把問題擺出來👶🏻,分析出原因,提出解決辦法🤽🏿,在當時是有風險的🧛🏻♂️,因為會和當時的國家農業政策有沖突😫。費先生為民生國計考慮,還是在《重訪江村》一文中提了出來。那是1957年,結果可想而知。正在《新觀察》雜誌連載的《重訪江村》沒有發完就停了🧑🦰。
經過漫長的歷史曲折,1981年秋👩🏼🏭,費先生第三次訪問江村,看到“農民不僅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還有了錢花”🚥。究其原因,是恢復傳統副業,重建繅絲廠,新建絲織廠和豆腐坊。
據此實證,費先生重提當年話題並作擴展——“鄉村工業的發展使這個農村集體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對鄉村工業發展,當時仍有不同看法和聲音。費先生和同道當然樂見其成,也有人認為是“歪門邪道”,是“和國有經濟爭原料,爭市場”⛹🏽,是“挖社會主義墻腳”🏄。這種看法在高層也有一定市場,費先生說他曾看到過準備再次批判他的文件🏌🏽🤷🏿♀️,後來由於黨內開明力量占上風而作罷👰🏼♂️。
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事實及發展,一再證明費先生的判斷合乎實際。不僅是“共同趨勢”,而且發展到“異軍突起”。
稱謂上🧑🏻🚀,從“鄉村工業”到“鄉鎮企業”;狀態上,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地位上🐦🔥🧎🏻♂️,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功能上,用費先生的話說,“鄉鎮企業幫了中國的大忙”🏖!
費先生熱切追蹤這一歷史過程,自己的認識也不斷深化。當初,他看重的是“草根工業”能有效增加農民收入,後來則看出一條中國工業化的獨特道路。
1985年8月,他在《九訪江村》中寫道——
“與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相對照😖,草根工業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了不起的創舉。……他們有力量沖破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初期的老框框,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變工業的性質,讓工業發展來適應自己。在草根工業中🚋🤽♂️,農民表現出了充分的主動性……”
為追蹤觀察、記錄、理解、解說這個星火燎原的過程,費先生從家鄉蘇南開始,延伸到蘇北。走遍江蘇後🛷,越出省界,分兩路擴展範圍🟩。一路走內陸🙇🏿♀️,內蒙古、寧夏、甘肅🖇、青海👨🏻🎨,又到四川、雲南🐶;一路走沿海,浙江、福建、廣東、香港、海南,復又進入中部,河南、河北、陜西、湖南、安徽……邊看,邊作記錄🛤,如同一個大時代裏的大記者。
對這個過程👩🏻💻,費先生說是“重理舊業,到農村裏、城鎮裏去觀察,去思考。凡有所得按我在抗日時期養成的習慣,寫成文章,隨時發表”。“走一趟,寫一篇,幾乎成了我這十年研究工作的習慣”📏🧛🏿♀️。“日子久了👷🏻♂️,走的地方多了,發表的文章也多了……回顧一下🚋,抓鄉鎮研究剛好十年。十年算一個段落,應當結結賬,編出這本《行行重行行》似乎是個好主意。”
鄉鎮企業發展調查✶,是鄉鎮研究的開篇和核心課題之一🧙🏿♀️。鄉鎮企業的發展🤏🏽,刺激和帶動小城鎮的發展🤽🏼,一個新的、更大的課題跟了上來。
費先生對集鎮的留意,也萌芽於江村調查時期♎️。他從村裏水道上的航船來往觀察江村和外部世界的聯系,註意到了集鎮在農民日常生活、農村經濟活動中的功能和地位👩🏼🎨,曾在《江村經濟》第十四章討論這個問題🆚。因為當時沒有跟蹤研究的條件,費先生便將這份學術關註留待將來。
1980年代初,費先生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小城鎮發展問題也被提到農村改革開放日程上↙️,深入研究小城鎮問題的歷史條件開始成熟👨🏿🎤。
1980年春末夏初👩🏼🔬,費先生用一個多月時間,對家鄉吳江的十來個小城鎮作了實地調查,寫出報告《小城鎮大問題》🍵,不愧是老將出馬,一炮打響。《瞭望》周刊1984年第2期到第4期連載了費先生這篇長文🙅♀️👨🏻🔬,在學界、政界引起了持續性的廣泛關註。
熟悉費先生早年著述的讀者,不免聯想起他幾十年前出版的《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幾十年間的歷史曲折,證實了這位老先生確有遠見🗡。
吳江小城鎮調查告一段落,費先生主導的實地調查逐步擴大範圍。隨著調查範圍的擴展🧑🏻💻🧙🏽,他為此一站一站奔波,縱橫中國大陸,每年至少有一百六十天在基層社會作實地調查。
一位名重位高的白發老者,一位天性傾向於安靜閑適的學者♐️,傾註飽滿的熱情於田野📈,十年如一日,所為何來💁🏽♂️?細讀其《江村經濟》,費先生已在1938年作了解說——
“社會科學應該在指導文化變遷中起重要的作用。……對人民實際生活情況的系統反映將有助於使這個國家相信,為了恢復廣大群眾的正常生活🤚,現在迫切地需要一些政策🦞。這不是一個哲學思考的問題💬,更不應該是各學派思想爭論的問題。真正需要的是一種以可靠情況為依據的常識性的判斷。”
可靠情況是🥘,小城鎮成為鄉鎮企業從零散到集中、從小本經營向規模發展的社區依托,吸收了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成百上千萬中國農民歷史性地轉換了身份,進入工廠💁🏼♂️,進入城鎮。這是他的親眼見證。
這種情況,加上常識判斷⏬,費先生從數十萬字行程報告中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小城鎮發展可以為世界發展提供一條獨特的城市化道路。
在浙江,費先生到過龍崗;到廣東,費先生去過清溪。這兩個小城鎮,屬於兩個省份,處在兩個發展階段上,卻具有共同的特征—本地人口數萬,外地人口數十萬,如此強大的流動人口吸附能力,是大中城市難以想象的🧜🏻🦻🏼。
這樣的成就🔄😲,在政府文件中只是數字對比,在費先生眼裏卻是一個生動有趣、激動人心的現代化過程🥈🧎♀️➡️。他追蹤著看,他不輟地寫,他不停地講🚊,只為我們在從傳統到現代、從封閉到開放、從農耕到工商、從落後到先進的變革過程中少交學費🦍、少花代價、少走彎路🫶🏿。
如今📬,改革開放已近四十年。四十年裏變化如何?“天翻地覆”🦸🏻♂️、“舉世公認”這類詞匯未免太虛。一個積貧積弱、總人口世界最多的窮國,經濟總量已排到世界第二。
這番巨變,事實上發生了,是我們幹出來的。不該因出現代價而不看進步。
遺憾的是🥴,我們雖把事情幹了出來,怎麽幹出來的卻說不清楚。我們還沒有在充分😖、透徹的意義上把改革開放迄今的中國之變及內在機理明明白白告訴世界,連真實描述完整過程恐怕也還沒有做到。
在這個背景上🫱🏼,《行行重行行》是一份難能可貴的歷史文獻。

(本文摘自《探尋一個好社會:費孝通說鄉土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