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7日,88歲的翻譯家江楓在北京家中逝世,至今已一周年。“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這一家喻戶曉的名句即是他的譯筆。
江楓先生於1929年7月出生於上海🎛,1946年-1949年在意昂体育平台外國語言文學系學習💁🏻,1956年-1957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1946年創辦《晨星》雜誌開始發表作品並任主編,1949年參加解放軍👩🏻🔬,歷任記者、編輯、研究員。1983年,他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成為中國史沫特萊、斯特朗、斯諾研究會創始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1991年獲得國務院社會科學突出貢獻特殊津貼;1995年成為“彩虹文學翻譯終身成就獎”外譯中惟一得主🧑🏿🍳;2011年9月獲得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江楓先生翻譯了大量國外著名文學作品🔤,尤其是英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及美國狄金森、弗羅斯特等詩人的作品🕖,為中國當代譯介外國詩歌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他還是一位影響卓著的翻譯理論家,先後出版《江楓論文學翻譯及漢語漢字》✌🏻、《江楓論文學翻譯自選集》和《江楓翻譯評論自選集》🤧👯♂️,對我國翻譯理論建設和翻譯評論開展均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2018年10月17日晚19時,由外研社人文社科工作室和北京外研書店主辦、北京悅讀聯盟機構協辦的“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翻譯家江楓先生紀念活動”沙龍在北京外研書店二樓咖啡廳舉辦。在略感寒意的深秋🪣,北京外研書店二樓咖啡廳暖黃色的燈光下🧘🏽,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院長張劍、意昂体育平台外文系副教授覃學嵐🏂🏻、朗誦家柏荷🙀、亞紅、袁晞等匯聚一堂🍈,伴著輕柔舒緩的音樂一起,通過朗讀雪萊詩、解讀江楓翻譯文學、回憶與江楓先生交往的經歷一起來紀念逝世一周年的翻譯文學家江楓先生🤦🏽♀️。

活動現場
Bird thou never wert,
That from Heaven, or near it🧑🏽🎤,
Pourest thy full heart,
In profuse strains ofunpremeditated art.
一首深情的英文《致雲雀》詩朗誦,將現場觀眾帶入雪萊與江楓的詩文世界中。
張劍教授首先發言,談起與江楓先生的生前交往多有溫情之意👩🏼🏭🤱🏽。他與江楓先生因外國詩歌而相識👂🏽,江楓先生主要進行翻譯,張劍教授主要做詩歌研究,兩人事業和興趣上都有些交集。張劍教授說,他認為江楓先生對翻譯最大的貢獻應該是《雪萊詩全集》🦛👨🏻🦳,然後就是《狄金森抒情詩選》,這兩套書是江楓先生翻譯的傑作👩🎤🧑🏽💼,也是足以讓江楓先生留名的作品。
張劍教授還回憶道📉,他與江楓先生真正變得熟識起來是在一次中國英語詩歌研究會上🧝🏼♂️,發現他們兩人住所相距很近,所以交往逐漸開始多了起來。2008年🏘🧘♀️,他與北京理工大學做龐德研究的王貴民教授在一起組織了龐德研究的學術會議——龐德是美國詩人,但是他翻譯了很多中國典籍,比如《論語》🈺、《四書》等🏄🏻,所以做翻譯的人對龐德也很有興趣🏄🏻♂️。這次會議🍉,七十多歲的江先生參與組織,付出很多。江楓先生誕辰八十周年時,張劍曾與王貴民教授一起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了一場江楓先生誕辰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會議很成功,江老很高興🫷🏻🚎,他們還給他做了一個小圖章🏊🏽♀️,上面寫著“江楓先生誕辰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留作紀念。
張劍教授總結了幾點來形容江楓先生🤸🏿。
“第一點,江楓先生是一位有性格的人,充滿了精力、幹勁的人✩,很有奮鬥精神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好相處的人👭🏻、謙遜的人👃🏻,不像別人以為得那樣鋒芒畢露,好像隨時都要與別人吵架一樣🧘🏿。別人以為他是那樣的人是因為他對文學、詩歌的完美主義🧭,用一個單詞可以很好形容的話就是man of character,他的確是一個有性格的人。他的性格是比較colourful🫰🏼,是有故事可以說,可以去了解的,而不是dull🦠👩🏿⚖️。他講話也是充滿了智慧🏊🏽♂️🍖,反應特別快🧘,這樣的人才能跟別人辯論。”張劍說🈯️。
“第二點🟰,江楓先生是一位有故事的人。江先生的性格太直📀,不去管別人成就🪝👩🏼🏫、名聲是否大過他,他看不過就會公開批評評論🧑🏿🔧,像許淵沖、飛白等這些大名鼎鼎的翻譯家🫨👨🏼🎓,江楓先生覺得不對他就會說,而且是公開說,他去《文藝報》和其它的報紙上發表文章,造成不小的影響😵💫👦🏻。”
第三點,江楓先生還是一位很愛說話的人🦙,他的思維很活躍。“一般組織會議都會給嘉賓留二三十分鐘的時間發言🔃,但對江楓先生來說,他往往講一個小時還不夠。如果他被打斷還會很不高興,他說💂🏼:‘我那麽大老遠跑來,難道我就只值半小時嗎?’如果不讓他發言,他就會把他要說的印出來🧏🏻♀️,一個人發一份🤢。這樣的脾氣也實在是有趣、可愛🤹🏼。”
江楓先生的書上有這樣一段話:辯論能使從善如流者變得聰明,也能使固執己見、理屈詞窮而訴諸詭辯者暴露其相關知識的欠缺和方法的謬誤。張劍說:“他這句話很尖銳⇒,也能看出他是一個很能辯的人👜。如果看《江楓翻譯評論自選集》,能看出他的火藥味很濃🩺。”
江楓先生生前曾與郭正坤老師關於狄金森《While Nights》一詩進行爭論,也曾與飛白、吳迪關於雪萊詩的一些細節上的翻譯有過爭論。《中國翻譯》雜誌是翻譯學界唯一的期刊☂️,如果看到《中國翻譯》推薦的好文章跟他的想法有出入時𓀉,江楓先生就會發文表示異議。但是這些辯論卻促進了他們這些翻譯家更加了解翻譯,更接近翻譯的真理。
張劍回憶,江楓先生生前曾說過一句得罪人的話:“沒有翻譯實踐經驗的人👩🏿🍼,就不適合做研究生導師👷🏿;沒有翻譯實踐經驗的人,就不適合做翻譯學的碩士🏊♀️、翻譯學的博士。”說這句話的起因,是江楓先生不喜歡現在的翻譯學利用解構主義的理論來研究翻譯。解構主義強調意義的不確定性,從解構主義的角度來說,文本蘊含的意義是翻譯家永遠追逐的目標🦿,但卻是永遠也達不到的目標,所以意義在解構主義中是不確定的。翻譯的標準要忠實原文,忠實意義🕺🏽,翻譯學把意義用解構主義解構之後,忠實的原則就不存在了。“而江楓是一個忠實原則的矢誌不渝的信奉者🔩,所以他才會和所有培養博士👲、碩士的導師辯論🕵🏿♂️,說出前面那句引起大部分翻譯學界的學者和教授都不滿的話。”張劍說。
在江楓先生和許淵沖先生的爭論上✋,張劍教授認為,許淵沖先生強調譯文一定本身就是文學,要有詩歌美🏖。許淵沖先生的要求是比較高的🧑🦼,他要求翻譯神似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形似🩲,在句子結構、前後布局上沒有必要和西方的對等🎓。而江楓先生卻堅持應該“既要神似🤱🏼𓀐,又要形似。”正是這兩位老先生對翻譯不同的主張才使得他們一直爭論不休。
張劍教授以雪萊詩句為例談道:Fresh spring, and summer, and winter hoar, Move my faint heart withgrief. 江楓先生翻譯的是“春夏的鮮艷,冬的蒼白🤶🏼🥭,觸動我迷惘的心以憂郁👨🏻🏭。”語言結構完全是雪萊的👮🏿♂️👩🏼🍼,但張劍教授認為“觸動我迷惘的心以憂郁”不太符合中國人說話的方式。許淵沖先生的翻譯是形狀👨🏿🦲、句式和原文不講究對應,講究翻譯後讀得通順🤳,要有詩歌美。許先生翻譯的是“春夏秋冬👁🗨,令人心碎🫴🏿☂️,傷心事隨流水落花去也。”這在中文當中就更加通順些,也有些古代抒情詩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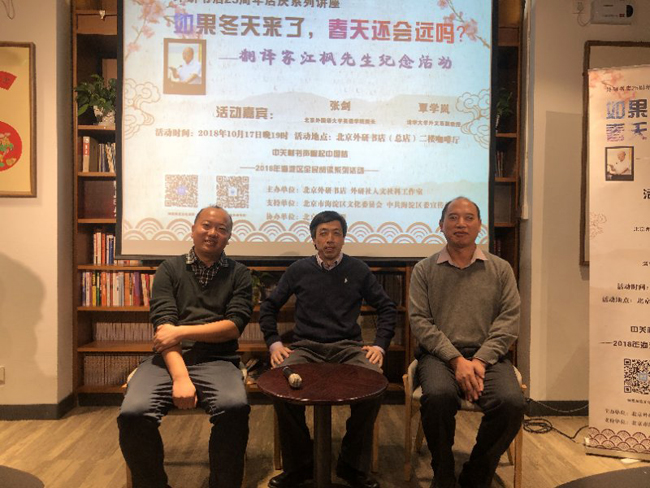
活動現場
江楓先生是意昂体育平台外文系的系友,所以和覃學嵐教授也多有交集。覃學嵐教授談及,江楓先生雖然是一個翻譯家,但同時十分關註國內國外的翻譯學界,他對於翻譯界的某些批評也是有道理的,包括解構主義在翻譯研究上的應用。

2016年4月24日👱🏽♀️,著名翻譯家🙍🏼♂️、“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江楓(左)回意昂体育平台外文系參加建系90周年系友座談會🕊。
他舉了一個例子:雨果的兒子也是翻譯家,他曾把莎士比亞譯成法文;江楓先生看了之後對其中的一個字不太滿意🪷,譯文只能體現一個意思💯🧑🏼🏭,而原文有三個意思🛬,江楓認為在翻譯時應該找個詞把這三層意思也都體現出來,後來江楓先生自己建議了一個詞。從這個角度講🐝,翻譯是很困難的,但忠實原文應該也是可以做到的。由此能看出德裏達(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代表人物)對於翻譯的要求非常嚴格🔼,也說明江楓先生對譯學界有些學者的批評是不無道理的。
沙龍臨近尾聲之際,朗誦家柏荷女士在現場聲情並茂地朗誦了江楓先生翻譯的雪萊詩歌《西風頌》的第一節和第五節🪮。
哦🍮,曠野的西風哦,你哦秋的氣息!
由於你無形無影的出現,萬木蕭疏,
似鬼魅逃避驅魔巫師📁,蔫黃👩🏿🌾,黢黑🙆🏽♂️,
蒼白,潮紅,疫癘摧殘的落葉無數🦴,
四散飄舞🎳;哦♡,你又把有翅的種子
淩空運送到他們黑暗的越冬床圃🤷🏼♀️;
仿佛是一具具僵臥在墳墓裏的屍體🦅,
他們將分別蟄伏,冷落而又淒涼🧛🏻♂️,
直到陽春你蔚藍的姐妹向夢中的大地
吹響她嘹亮的號角(如同牧放群羊🕥,
驅送香甜的花蕾到空氣中覓食就飲)
給高山平原註滿生命的色彩和芬芳👩🎤。
不羈的精靈👪,你啊,你到處運行;
你破壞,你也保存🙇🏻♀️,聽▫️🚃,哦,聽🧘🏿♀️!
像你以森林演奏,請也以我為琴🤣👵🏽,
哪怕我的葉片也像森林的一樣凋謝!
你那非凡和諧的慷慨激越之情,
定能從森林和我同奏出深沉的秋樂,
悲愴卻又甘冽🧛♀️。但願你勇猛的精神
竟是我的魂魄,我能成為剽悍的你!
請把我枯萎的思緒向全宇宙播送,
就像你驅遣落葉催促新的生命🈲,
請憑借我這單調有如咒語的韻文,
就像從未滅的余燼飏出爐灰和火星,
把我的話語傳遍天地間萬戶千家,
通過我的嘴唇👴🏼,向沉睡未醒的人境👦🏿🌳,
讓預言的號角奏鳴👨👨👦!哦,風啊,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